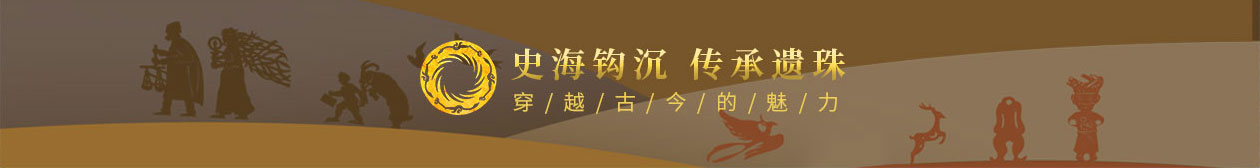清代蔓草蝴蝶纹蜀锦(丝织品)
四川博物院工艺美术馆藏
清代的印染织绣工艺比之明代有更大规模的发展。由于传统的积累,同时伴随著社合生产力的提高和需求量的扩大以及时代审美趣味的转换,生产技术日趋进步,品种花色愈益繁多,除实用品的生产外,陈设品的数量急剧增加。
入清后,四川的丝织业从明末战争破坏的状况中得以恢复,成为仅次于江浙和广东的第三大蚕丝产区。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年间,四川州县官府大力提倡栽桑养蚕,发展丝织业,使蚕业迅速恢复发展。“蜀中墙下树桑,宅内养蚕,习以为常”,同时内外贸易频仍,宣统三年(1911)《广安州新志》载:广安正街多“锦、绮、绫、罗之凑。大石、罗渡、花桥、观音阁等场,市易布帛”。清末十年间是成都丝织业最为繁盛的时期,每年可产各种绸缎55万匹,值洋990万元,“产品行销陕、甘、豫、晋、冀、赣、云、贵、青各省,其它各省亦间或有之”。
清代中叶,四川丝织业由原来相对集中在川西、川北地区,发展到川东、川南。丝织名品除蜀锦外,重庆的巴缎、乐山的嘉定大绸闻名全国,南充的花素绸、花绫、湖绉和阆中的川北大绸都是当时的名品。
四川丝织业以成都、嘉定(今乐山)、顺庆(今南充)、保宁(今阆中)、潼川(今三台)、重庆为最盛。
清初成都丝织业濒于绝境,康熙中期,有数百名逃滇织工归返成都,重理旧业,成都的丝织业得以绝而复苏。到乾嘉年间丝织业渐趋繁荣,规模扩大,产量增加,工艺进步。1850年,成都丝织业获得了一个发展大机会。由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太平军先后攻占了位于江南的南京、苏州、杭州等重镇。受此影响,清政府设在宁、苏、杭三地的织造局相继停歇。作为权宜之策,“清廷乃移织造府贡货于成都办理”,与此同时,此前为皇宫织造丝绸贡品的部分工匠亦由江浙西迁至成都。成都“有机房二千处,织机万余架,机工四万人”,可织造锦、缎、绸、绫、纱、罗、绉、绢等20种丝织品种,以织技精巧,纹样优美,色彩艳丽而独具地方特色。最盛时,成都的丝织品“供全省之用,并销陕甘云贵”。“城内百工咸备,皆有裨益于实用,其精巧者,无过乎制造。有宫绸、宁绸、线缎、偻缎、闪缎、线绉、薄艳、平沙、明机蜀锦、天心锦、洗花绢,龟兹栏杆(花边),每年采边运京,以供制造之不足。
重庆府的丝织业在乾隆年间也兴盛一时,乾隆五十九年(1794),重庆城内有“绸号四十余家,系贩自卖,机房二百余家,色绫系伊等自织”。
19世纪上半叶,嘉定府丝织业拥有几百台大型织机,年产绸缎10万匹,其中嘉定大绸和花绫等精制品达到2万余匹。顺庆府机房约30家,除织造花素绸外,还生产花绫、湖绉。雍、乾间.“嘉定、保宁、成都每岁所出之丝,获利不下数百万金”。
明末清初,重庆巴县一带,“纺花手摇车家皆有之,每过农村,轧轧之声不绝于耳”。合川一带,丝织业发达,清朝中叶,太和镇在清朝中叶已发展为以丝织业为主的特色场镇。
清朝初期,生丝是四川两大主要的出口商品之一,另一种是药材。四川各地生丝行销全国各地。在成都西南的朱雀镇,丝店林立,各地来的丝客,都投到丝店,以丝求售。重庆綦江丝市“则大聚于抉欢坝,每岁山陕之客云集,马驮舟载,本银约百余万之多”。郫县每岁蚕日,“有商来收茧取丝,至成都销之”。新津县“邑人喜蚕桑,故三月丝市,以新津为最”。
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蜀锦,由于明末清初四川战乱的破坏,“锦坊尽毁,花样无存。今惟天孙锦一种,传为遗制云”。到了康熙初,蜀锦生产才逐渐恢复,至乾隆、嘉庆朝,蜀锦织造技艺及生产蜀锦的机具小花楼木织机功能更趋完善,染织技艺也达到炉火纯青地步。蜀锦产量大增,交易甚为繁荣。“城内百工咸备,皆有裨于实用。其精巧者,莫过于织造”。宫廷采购大增,从同治四年(1865年)至光绪二年(1876)织造府共计在四川采办锦缎七次,仅1876年,即“令四川采办锦缎绉绸等件二千九百余匹”。
清代蜀锦纹样仍仿唐宋,但大量采用如意、博古、龙凤、婴戏和福禄寿喜、梅兰菊竹为题材,别具一格。同治年间(1862—1874),由于受到江浙先进织造技艺的影响,蜀锦在锦样设计上出现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三绝”,即“方方”“雨丝”、“月华三闪”三种新样式。它们把传统的彩条色彩变化成色彩旋律艺术,并与创新装饰艺术结合起来,采用了多彩叠晕的艺术,在丰富的色相、柔和的光晕中点缀着各式各样的图案纹样,使锦样有更加奇异华丽的艺术效果,蜀锦史上谓之“晚清三绝”。1908年蜀锦参加南洋博览会,获得“国际特奖”。清代蜀锦受江南织锦影响,产生了月华锦、雨丝锦、方方锦、浣花锦等品种。到清末,成都机坊已达两千处,织机万余架,机工四万多人,在乐山的苏稽、白杨坝等场镇几乎是家家有织机,户户出丝绸,蜀锦生产又发展到一个短暂的黄金时代。蜀锦的织造工艺相当精细,到清末更被美称为“蜀江锦”了。
从现存四川省博物馆的一台嘉道织机可以看出,当时织锦机械的制造结构之精密,布局之巧妙。机器除少数铁部件外,多用竹、木制作,通高3.4米,机长5.15米,可以织出宽66厘米的八枚锻纹平纹现花龙风雨丝花面。这种织品鲜艳华丽,至今为人称绝。四川省博物馆收藏的一幅清代“八答晕”锦,就具有独特的工艺水平。
由于丝绸产品的贵族化,清代丝织工艺基本放弃了印染,把重点集中在了织绣上。清代的宫廷服饰大部分均用刺绣加以装饰。清代刺绣运用之广、针法之妙、绣工之精巧,为历代所不及。在这些地方绣中,最著名的是以苏州、广州、长沙、成都为集散中心的“苏绣”“粤绣”“湘绣”“蜀绣”,合称中国的“四大名绣”。
因蜀州而得名的蜀绣,明末清初的数十年间,由于张献忠“血洗四川”、“清军入川”以及“三藩之乱”,接连不断的战乱、瘟疫及天灾,四川境内人口锐减,蜀绣行业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至清朝的统治稳固、社会太平后,蜀绣才得以逐渐恢复。蜀绣特点是多平直绣花,颜色明快鲜丽。
清朝中叶以后是蜀绣的全盛时期,逐渐形成商品行业生产,尤以成都九龙巷、科甲巷一带的蜀绣为著名。清道光十年(1830),为了维护刺绣行业共同利益,调解内部纠纷,促进蜀绣的兴旺发展,刺绣业组成商业行会性质的“三皇神会”,包括店铺商人、领料人、技术师傅三个行业。刺绣主分三类:穿货、行头和灯彩。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又在成都成立四川省劝工总局,内设刺绣科,还招聘男性工人,同时聘请名家设计绣稿,并钻研刺绣技法。这时的蜀绣除实用品外,更丰富了刺绣欣赏品类,包括条屏、中堂、斗方、横披等。题材除以古代著名文人画的作品为粉本,如苏东坡、郑板桥、陈老莲等的作品,也开始请当时名画家设计绣稿,一些名画家如刘子谦、赵鹤琴、杨建安、张致安等人的绘画作品也成为刺绣粉本,其后,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刺绣名家及著名刺绣作品,如张洪兴、王草廷、罗文胜、陈文胜等(注:仅见记载,人物生平事迹不详)。自此蜀绣在国内和国际不断获奖,如张洪兴等名家绣制的动物四联屏获巴拿马赛会金质奖章,张洪兴绣制的狮子滚绣球挂屏获得清王朝嘉奖。这些举措反过来又促进了民间刺绣业的商业发展,刺绣商号及绣铺逐步增多。清中期后,蜀绣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吸收顾绣、苏绣之长,发展成为名闻遐迩的地方性商品绣。
四川博物院藏有许多清代蜀绣作品,如《戏曲故事屏》、《盘金博古纹椅垫》、《人物故事蚊帐檐》、《百鸟朝凤蚊帐檐》、《仕女书画纹枕顶》等,构图层次分明,色彩典雅,针法细密,具有很强的装饰性,是蜀绣典型的民间风格。
其它品种屡有发展。如绸,18世纪中叶,嘉定府织造技术高超,生产出的“嘉定大绸”闻名全国,其中缎面提花花绫,乾隆时即已生产。南充花素绸、花绫、湖绉等也成为一方特产。保宁府等县生产的“川北大绸擅名蜀中”。如布匹,成都县有白花布、云布、紫花布、棉布”。清乾隆年间,棉织机坊在双流已是“各场有之”。嘉庆以后,农村妇女的纺纱,多数是为机坊加工,以纱易花,换取“补头”(机坊外敷的利花)。石柱直隶厅人民用自己生产的棉花“织为布,色不甚白,而坚牢耐久,谓之‘家机布’”。由于蓬溪盛产棉花,这里“其人勤纺织,布精好”。中江县“妇女又能纺织,故织者恒多。宽长者日‘大布’,曰‘连机’;小曰‘台正’。其佳者皆日‘卓’,劣者曰‘行’”。如毛纺织,雷波一带少数民族“造牛羊毛为毡衣,人披袭塞寒”。大金川一带藏民,“服饰多氆氇”。如棉布,新津棉布“有贩至千里外者”。如扎染,明清时四川的自贡、荣县等地都有各富特色的扎染工艺。扎染工艺并不复杂,只需通过对布帛进行扎、缚、缝、缀等手段,浸染后便可以获得变化多端的纹饰效果,这些品种远销各地,如荣昌夏(麻)布闻名遐迩,“山陕直隶各省客商,每岁必来荣购买,运至京师发卖”,隆昌夏布,别是隆昌细夏布,其使用价值超过丝绸,交换价值,亦超过丝绸。明清时期,隆昌夏布被列为宫廷贡品。夏布有古代纺织品“活化石”之誉,其由半脱胶苎麻纤维手工纺纱织造而成,因其夏季穿着透气排汗、凉爽宜人,故称“夏布”。2008年荣昌夏布织造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
清代以来,全川普遍种蓝制靛,染坊林立。丝织品的染色技术也有了提高。如当时流行的浅红、大红、谷黄、古铜、鹅黄等色,均居上乘。
毛纺织业逐渐恢复,毛毯、毛毡、毛氆氇等,在少数民族地区普及。藏族地区的藏毯工艺,别具风格,最引人注目的是上面的图案。游龙、快鹿、翔凤、飞蝶、山水花草,或动或静,或腾空驾云,或吞云吐雾,或戏水弄花,栩栩如生。色彩鲜亮夺目,图案简练明快,富有立体感。这些织毯工艺品,小的仅40厘米见方,大的可织成10多平方米。它们既是藏族织染技艺的荟萃,也是藏族民间美术的杰作。
明清时代,刺绣已在羌族地区盛行,后来挑花亦渐普遍,并为羌族妇女所擅长。羌绣不同于以地域命名的中国“四大名绣”,它有着一些独特针法技艺,在用料选材、纹饰图案及色彩规范上,都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在我国工艺美术界独树一帜。四川羌族刺绣,在四川民间刺绣工艺中有“南彝北羌”之说。不过,羌绣之来源尚无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四川羌族刺绣与蜀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在阿坝,嘉绒藏族织绣工艺可以追溯至唐蕃政权时期,清中叶,乾隆征伐大、小金川以后,汉族移民进入嘉绒地区,随之带来了汉族地区的挑花刺绣技艺,嘉绒藏族在原有织绣的基础上,吸纳了更多的汉地挑花刺绣技艺,致使嘉绒藏族织绣技艺更臻成熟,自成体系,并一直传承至今。
别斯满位于阿坝州小金县东北,清乾隆出兵金川后,在此建立别思满屯,为美诺厅所辖四屯之一。在嘉绒地区最为独特的服装,就是别斯满的满藏融合式女子礼服。别斯满女子礼服,在挑花织绣技艺上受满族服饰风格影响,保留了传统的几何、花卉、雍忠等民俗图案,丝线色泽搭配突破传统大对比色调,色泽搭配和色泽过渡更有层次感,更加流畅优雅。与之相应,刺绣技艺也显得格外细腻生动。
凉山彝族的彝绣是彝族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彝族服饰文化的灵魂,技法主要有:刺绣、挑花、锁花、盘花、穿花、帖花、镶嵌等。
土家族传统织锦西兰卡普。元、明、清时期,四川秀山、酉阳、黔江以麻织“斑布”,“石柱……人织斑布为衣”。它是以棉纱为经线,采取通经断纬,反面挑织的方法,靠着土家姑娘一双灵巧的手,用一只牛骨挑针,在古老的斜织机上手工织成的。
据统计,1907年成都劝工会商品中,许多地方都有产品,如崇庆(今崇州)绸缎、印花,什邡刺绣,邛州(今邛崃)丝织品,涪州(今重庆涪陵)刺绣,南充丝巾、绸缎,绵州(今绵阳)绸缎,等。在简州(今成都简阳市),为使蚕丝力求改良,还开设了蚕丝展览会。
四川(含重庆)现藏清代印染织绣珍品如下:
水月观音发绣,成都文殊院藏,为清代道光五年陕西总督杨遇春之女所绣。发绣,即运用头发绣制的绣品。此发绣观音长144厘米,白色素缎为底。图中主像为一屈右膝坐于水边石矶之上的观音大士,观音头发前倾,戴有发箍,面微右侧,双目略下视,身着袈裟。像右侧石矶上还绣有一净瓶。像后绣紫竹一丛。绣像神态庄严、恬静,线条流畅、生动,线法熟练谨严,堪称发绣精品。
羌族花腰带,四川博物院藏,质地为羊毛,花带中间织有黑色几何图案,黑红色,淡绿色边,两端有流苏。羌族传统服饰腰带多用麻布或羊毛织成,上绣花卉图案。
羌族云肩,茂县羌族博物馆藏,质地为丝绸,以拼贴、刺绣、编织等工艺制成,用藕粉色、淡绿色拼贴成云纹,中间以蓝色丝线刺绣梅、兰、竹菊图。
《前出师表》绣屏,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长193厘米,宽43厘米,黑底白字,古朴厚重,文字刚劲有力,绣品有毛笔书写之笔锋,针脚平齐如刀切一般。系1953年西南文教部拨交。
马蹄袖蓝纱绣龙单衣,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衣长139厘米,袖长90厘米,系1953年西南公安部拨交。
清代藏族彩绣白度母唐卡,四川博物院藏,长30厘米,宽23厘米。
四川博物馆现收藏有清代蜀绣多种:天蓝缎地戏曲故事屏4幅、红缎地盘金博古纹椅垫、白缎地人物故事蚊帐檐、绿地人物故事蚊帐檐、红缎地百鸟朝凤蚊帐檐、红缎地仕女书画枕顶、白缎地花卉纹枕顶、白缎地花蝶纹枕顶、白缎地盘金人物故事图枕片、红缎地五子夺魁图镜心,等。
本文摘自《四川美术史》(下册.元明清卷,巴蜀书社2020年)第937—945页。

唐林,美术史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四川历史研究院学术委员,四川省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四川非遗协会专家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个人独著《四川美术史》上、中、下三册(共320万字),为北大、清华、人大、南大、川大和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等众多著名大学和省市的图书馆馆藏。